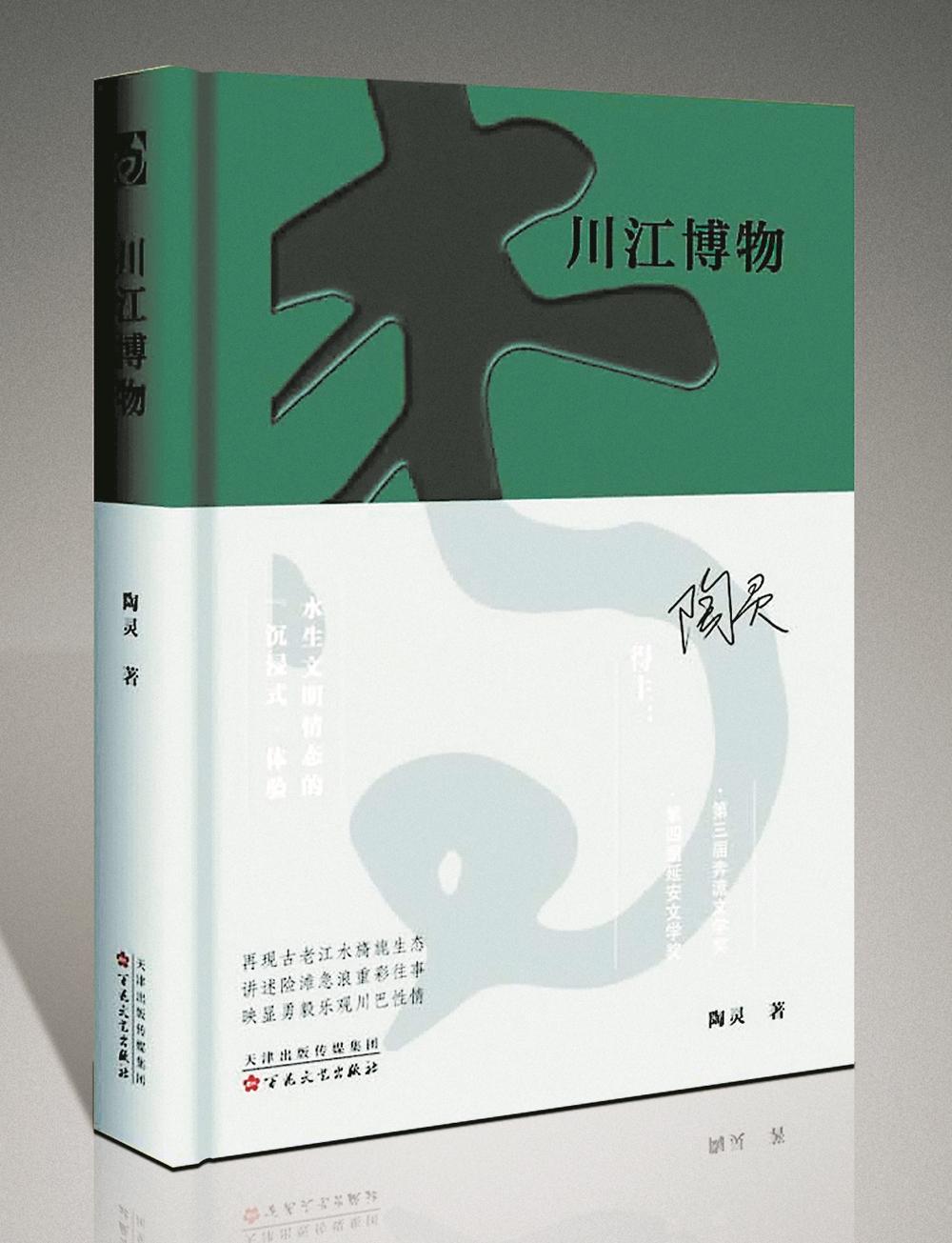□陶灵
我家门前就是长江。长江在我们那一段称川江,全长约1033千米,江流湍急,险象迭生。而雄伟、壮丽、峻险的长江三峡也位于其末端。因此,注定了川江的非凡与卓绝。
我一岁半时有了个妹妹,父母便把我寄养在二姑家,直到6岁。二姑住在距离县城30华里的一个千年古镇上,清澈的汤溪河水从镇中间奔腾而过,蜿蜒向南流去,汇入了川江。冬天的时候,汤溪河边常停靠着几只木船,篾席棚中偶尔走下一个赤裸下身的桡胡子,光着的脚后跟裂开一道道血口,上身穿一件没了扣子的破旧棉袄,用草绳系住腰,双手抱着插进怀里。腋下一边夹着裤子,一边夹着空酒瓶,抖索着朝小镇走来。接近小镇那坡石梯时,赶忙穿上腋下的裤子。打完酒回船,刚下完石梯,马上把裤子脱下。这个镜头一直留在我脑海里。
1985年,我第一次出三峡。当时已进入川江汛期,瞿塘峡口的江面上无礁石阻流,相对平时宽阔而水流平缓。轮船“呜”的一声清脆长笛后,静静驶入峡口巍然屹立的夔门。我随旅客涌向船头甲板,擎天绝壁仿佛隔绝了一切嘈杂、喧嚣、烦躁,听不见风声,也不闻水响,就连身旁旅客对夔门的赞叹也在这独自宁静中被融化了。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厚重、凝练和深邃的自然与文化相融合的气息。从这一刻起,我的灵魂再没离开过三峡,再也没离开过川江。
于是,我写出了一些关于川江的文字,《汤溪桡胡子》《三峡船歌》……等几十篇。
比如《鱼钩》:
古巴人打仗时,为鼓舞士气,要敲打一种青铜铸成的圆桶形军乐器,叫“錞于”。錞于顶部铸刻着鱼、船、鸟、蛇、人面及菱形回纹图案,因不能完全解读其意,归类为“巴蜀符号”(或称“巴蜀图语”)。这些符号简单、抽象,唯独鱼图案具象刻画,头尾、嘴眼、鳞鳍俱全,非常逼真。明末清初时的文学家李渔说(译成白话),“鱼产卵,多得像粮仓里的小米一样,都装在一肚里。”鱼,腹大多子,作为“巴蜀符号”,寓意在其繁衍生息。民间盼多子,战场愿兵多。
民国初年,云阳汤溪河一个姓郭的乡绅立下乡约:凡是鱼产子期间,在汤溪河钓鱼,不罚钱,则重打板子。打板子就是打屁股。躺在板凳上,当着众人面,脱了裤子被打,又痛又受羞辱,十分长记性。俗世俗人俗事。
我用一首短诗结尾:夜/水中一弯新月/鱼儿/不要忘了鱼钩。
比如《水流江河满》:
七八岁的时候,有一次在外面玩得很野,回家时姑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,地上的木盆里装着脏兮兮的肥皂、碱粉水。她把我拉过去,顺手用正洗的衣服呼呼呼地给我洗手洗脸,嗔怪道:看你!脏得像个打油匠了。
我的手脸被粗布衣服擦痛了,叫喊道:“这个水愣个脏。”姑妈立马回答:“脏?只有手脏水,那有水脏手的。”
比如《腊子鱼》:
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,巴县木洞一个渔民用滚钩捉到一条腊子鱼,很大,根本弄不上岸,只好用网罩住,跟它在江里游来游去。镇上一位姓许的老先生听说后,赶到江边,花钱买下这条鱼,要求把它放了。被解网后的腊子鱼并没有马上逃生,这时,奇妙的一幕出现了:它围绕渔船慢慢游了一圈,然后一跃而起,蹦出江面二三尺高,再才迅速游走。有个老渔民说,这叫“跳滩”,是腊子鱼在感恩。
上面所列举,应该是表达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吧!《川江博物》列入“自然文学”书系出版的意图我也理解了。
我本应继续写下去,但我想着去挣钱,“下海”了,20年间没提过笔。再次握笔时,川江已完全变了模样:三峡中筑起大坝;普通客运轮船停航;木帆船绝迹……我还没来得及去拜访,川江有名的“号子头”走了,听说他临终前留下话:灵堂不放哀乐,放他唱的号子;墓碑上也刻一段号子。接着,三峡里被誉为“活化石”的102岁老驾长也走了,90岁时他还造了一艘机动船来开……
物非,人故。我抓紧时间,不断地沿岸寻访那些健在的老船工。他们满肚子故事,我原原本本搬进书里,甚至是原话,带劲、传神;有些船工不善言辞,但在一问一答中可获得许多印证;有时船工的几句俗语,又让我彻悟、识悟……
散文大家王鼎钧先生说:“一本书就是那个作者的世界……”
我的世界在川江。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