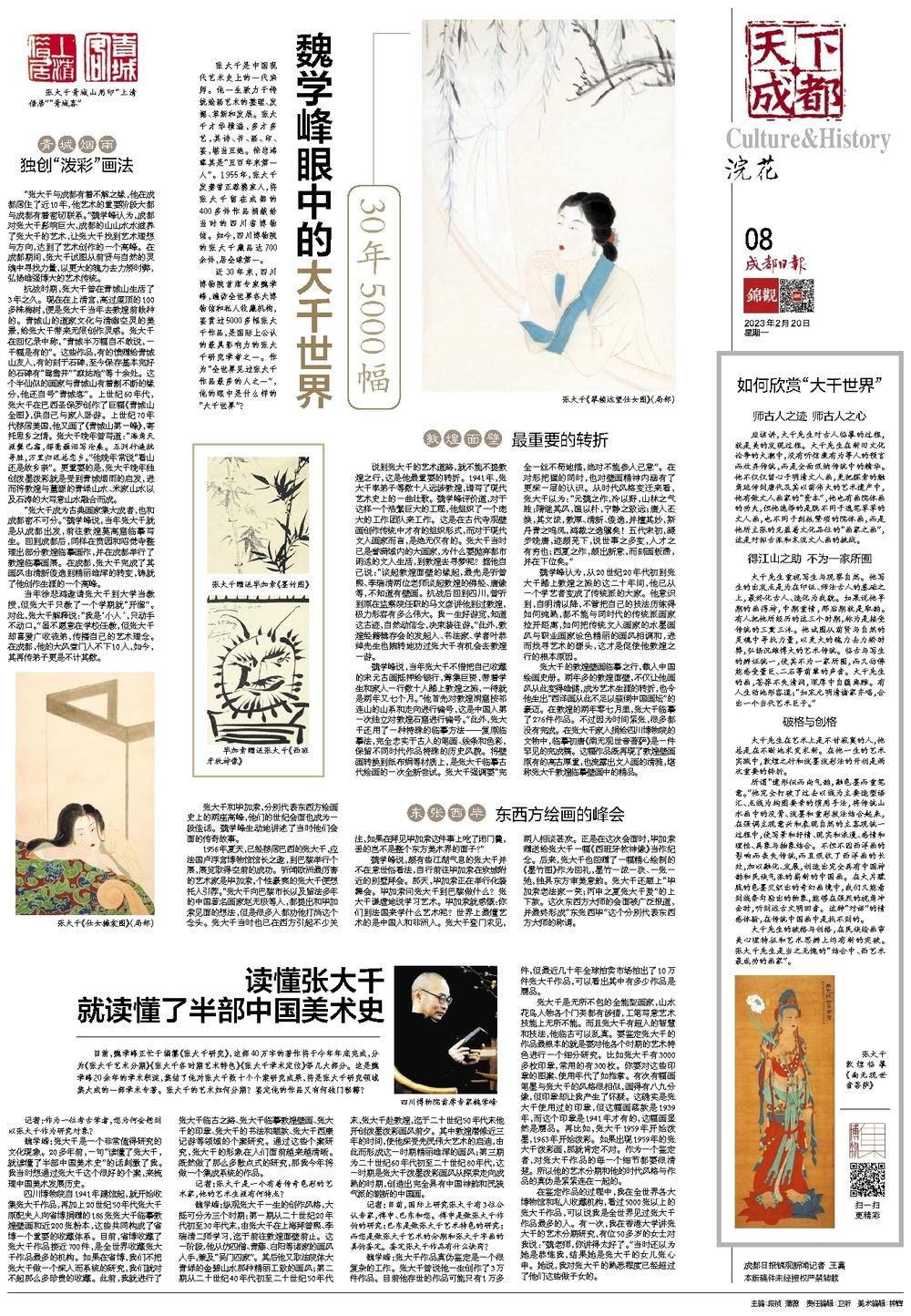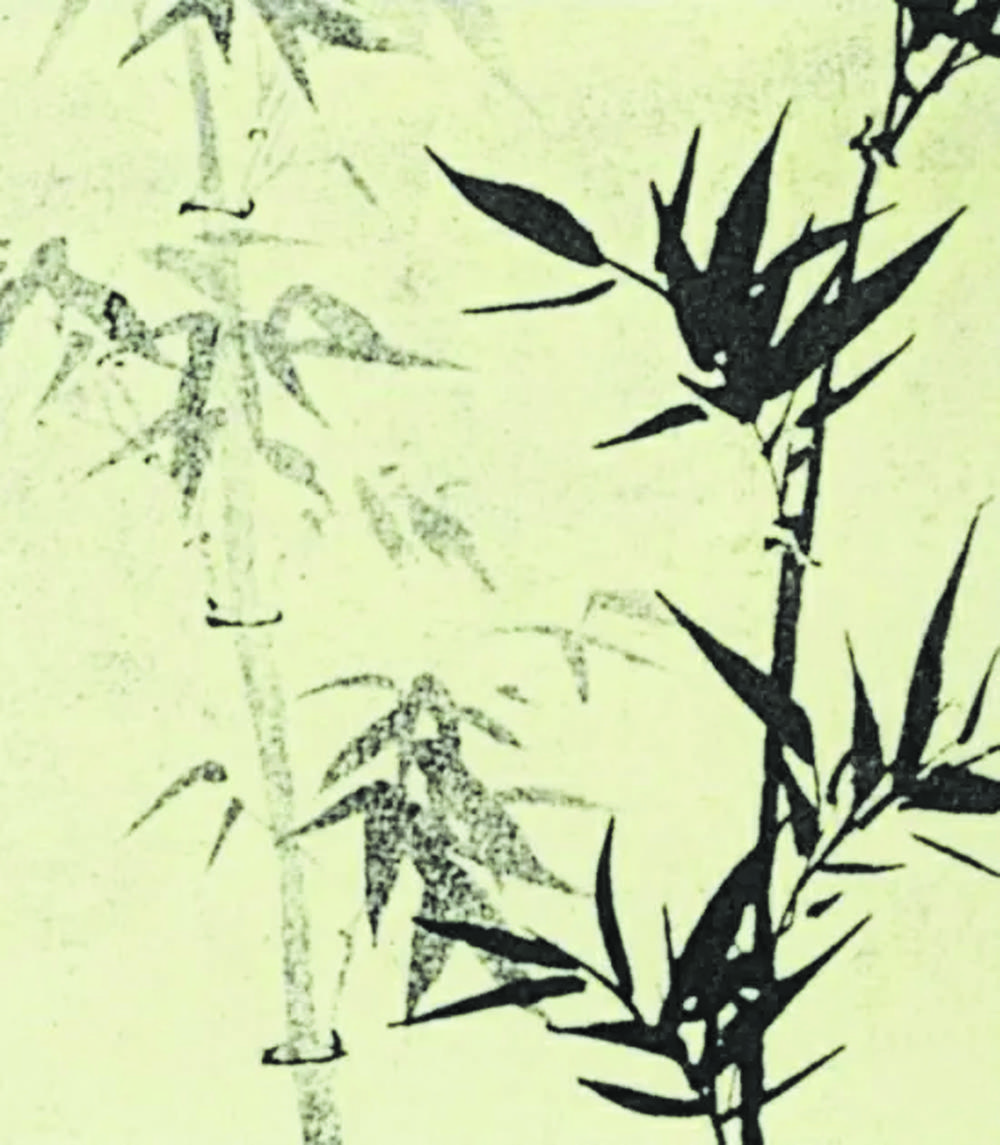张大千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代宗师。他一生致力于传统绘画艺术的整理、发掘、革新和发展。张大千才华横溢,多才多艺,其诗、书、画、印、鉴,堪当五绝。徐悲鸿尊其是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。1955年,张大千发妻曾正蓉携家人,将张大千留在成都的400多件作品捐献给当时的四川省博物馆。如今,四川博物院的张大千藏品达700余件,居全球第一。
近30年来,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魏学峰,遍访全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机构,鉴赏过5000多幅张大千作品,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张大千研究学者之一。作为“全世界见过张大千作品最多的人之一”,他的眼中是什么样的“大千世界”?
青城烟雨
独创“泼彩”画法
“张大千与成都有着不解之缘,他在成都居住了近10年,他艺术的重要阶段大都与成都有着密切联系。”魏学峰认为,成都对张大千影响巨大,成都的山山水水滋养了张大千的艺术,让张大千找到艺术理想与方向,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。在成都期间,张大千试图从前贤与自然的灵魂中寻找力量,以更大的魄力去力矫时弊,弘扬雄强博大的艺术传统。
抗战时期,张大千曾在青城山生活了3年之久。现在在上清宫,高过屋顶的100多株梅树,便是张大千当年去敦煌前栽种的。青城山的道家文化与清幽空灵的美景,给张大千带来无限创作灵感。张大千在回忆录中称,“青城半万幅自不敢说,一千幅是有的”。这些作品,有的馈赠给青城山友人,有的刻于石碑,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的石碑有“鸳鸯井”“麻姑池”等十余处。这个半仙似的画家与青城山有着割不断的缘分,他还自号“青城客”。上世纪60年代,张大千在巴西圣保罗创作了巨幅《青城山全图》,供自己与家人卧游。上世纪70年代移居美国,他又画了《青城山第一峰》,寄托思乡之情。张大千晚年曾写道:“海角天涯鬓已霜,挥毫蘸泪写沧桑。五洲行遍犹寻胜,万里归迟总恋乡。”他晚年常说“看山还是故乡亲”。更重要的是,张大千晚年独创泼墨泼彩就是受到青城烟雨的启发,进而将敦煌与董源的青绿山水、米家山水以及石涛的大写意山水融合而成。
“张大千成为古典画家集大成者,也和成都密不可分。”魏学峰说,当年张大千就是从成都出发,前往敦煌莫高窟临摹写生。回到成都后,同样在贲园和昭觉寺整理出部分敦煌临摹画作,并在成都举行了敦煌临摹画展。在成都,张大千完成了其画风由清新俊逸到精丽雄浑的转变,铸就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。
当年徐悲鸿邀请张大千到大学当教授,但张大千只教了一个学期就“开溜”。对此,张大千解释说:“我是‘小人’,只动手不动口。”虽不愿意在学校任教,但张大千却喜爱广收徒弟,传播自己的艺术理念。在成都,他的大风堂门人不下10人,如今,其再传弟子更是不计其数。
敦煌面壁
最重要的转折
说到张大千的艺术道路,就不能不提敦煌之行,这是他最重要的转折。1941年,张大千率弟子等数十人远涉敦煌,谱写了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曲壮歌。魏学峰评价道,对于这样一个浩繁巨大的工程,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团队来工作。这是在古代寺观壁画创作传统中才有的组织形式,而对于现代文人画家而言,是绝无仅有的。张大千当时已是誉满域内的大画家,为什么要抛弃都市闲适的文人生活,到敦煌去寻梦呢?据他自己说:“谈起敦煌面壁的缘起,最先是听曾熙、李瑞清两位老师谈起敦煌的佛经、唐像等,不知道有壁画。抗战后回到四川,曾听到原在监察院任职的马文彦讲他到过敦煌,极力形容有多么伟大。我一生好游览,知道这古迹,自然动信念,决束装往游。”此外,敦煌经籍辑存会的发起人、书法家、学者叶恭绰先生也婉转地劝过张大千有机会去敦煌一游。
魏学峰说,当年张大千不惜把自己收藏的宋元古画抵押给银行,筹集巨资,带着学生和家人一行数十人踏上敦煌之旅,一待就是两年又七个月。“他首先对敦煌洞窟按祁连山的山系和走向进行编号,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对敦煌石窟进行编号。”此外,张大千还用了一种特殊的临摹方法——复原临摹法,完全忠实于古人的笔画、线条和色彩,保留不同时代作品特殊的历史风貌。将壁画转换到纸布绢等材质上,是张大千临摹古代绘画的一次全新尝试。张大千强调要“完全一丝不苟地描,绝对不能参入己意”。在对形把握的同时,也对壁画精神内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从时代风格变迁来看,张大千以为:“元魏之作,冷以野,山林之气胜;隋继其风,温以朴,宁静之致远;唐人丕焕,其文浓,敦厚、清新、俊逸,并擅其妙,斯丹青之鸣凤,鸿裁之逸骥矣!五代宋初,蹑步晚唐,迹颇芜下,说世事之多变,人才之有穷也;西夏之作,颇出新意,而刻画板滞,并在下位矣。”
魏学峰认为,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张大千踏上敦煌之旅的这二十年间,他已从一个学艺者变成了传统派的大家。他意识到,自明清以降,不管把自己的技法历练得如何纯熟,都不能与同时代的传统派画家拉开距离,如何把传统文人画家的水墨画风与职业画家设色精丽的画风相调和,进而找寻艺术的源头,这才是促使他敦煌之行的根本原因。
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之行,载入中国绘画史册。两年多的敦煌面壁,不仅让他画风从此变得雄健,成为艺术生涯的转折,也令他生出“西洋画从此不足以骇倒中国画坛”的豪迈。在敦煌的两年零七月里,张大千临摹了276件作品。不过因为时间紧张,很多都没有完成。在张大千家人捐给四川博物院的文物中,临摹初唐《南无观世音菩萨》是一件罕见的完成稿。这幅作品既再现了敦煌壁画原有的高古厚重,也流露出文人画的清雅,堪称张大千敦煌临摹壁画中的精品。
东张西毕
东西方绘画的峰会
张大千和毕加索,分别代表东西方绘画史上的两座高峰,他们的世纪会面也成为一段佳话。魏学峰生动地讲述了当时他们会面的传奇故事。
1956年夏天,已经移居巴西的张大千,应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之邀,到巴黎举行个展,展览取得空前的成功。听闻欧洲最厉害的艺术家是毕加索,个性豪爽的张大千便想托人引荐。“张大千向巴黎市长以及留法多年的中国著名画家赵无极等人,都提出和毕加索见面的想法,但是很多人都劝他打消这个念头。张大千当时也已在西方引起不少关注,如果在拜见毕加索这件事上吃了闭门羹,丢的岂不是整个东方美术界的面子?”
魏学峰说,颇有些江湖气息的张大千并不在意世俗看法,自行前往毕加索在坎城附近的别墅拜会。那天,毕加索正在举行化装舞会。毕加索问张大千到巴黎做什么?张大千谦虚地说学习艺术。毕加索就感慨:你们到法国来学什么艺术呢?世界上最懂艺术的是中国人和非洲人。张大千登门求见,两人相谈甚欢。正是在这次会面时,毕加索赠送给张大千一幅《西班牙牧神像》当作纪念。后来,张大千也回赠了一幅精心绘制的《墨竹图》作为回礼,墨竹一浓一淡、一张一弛,独具东方审美意韵。张大千还题上“毕加索老法家一笑;丙申之夏张大千爰”的上下款。这次东西方大师的会面被广泛报道,并最终形成“东张西毕”这个分别代表东西方大师的称谓。
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