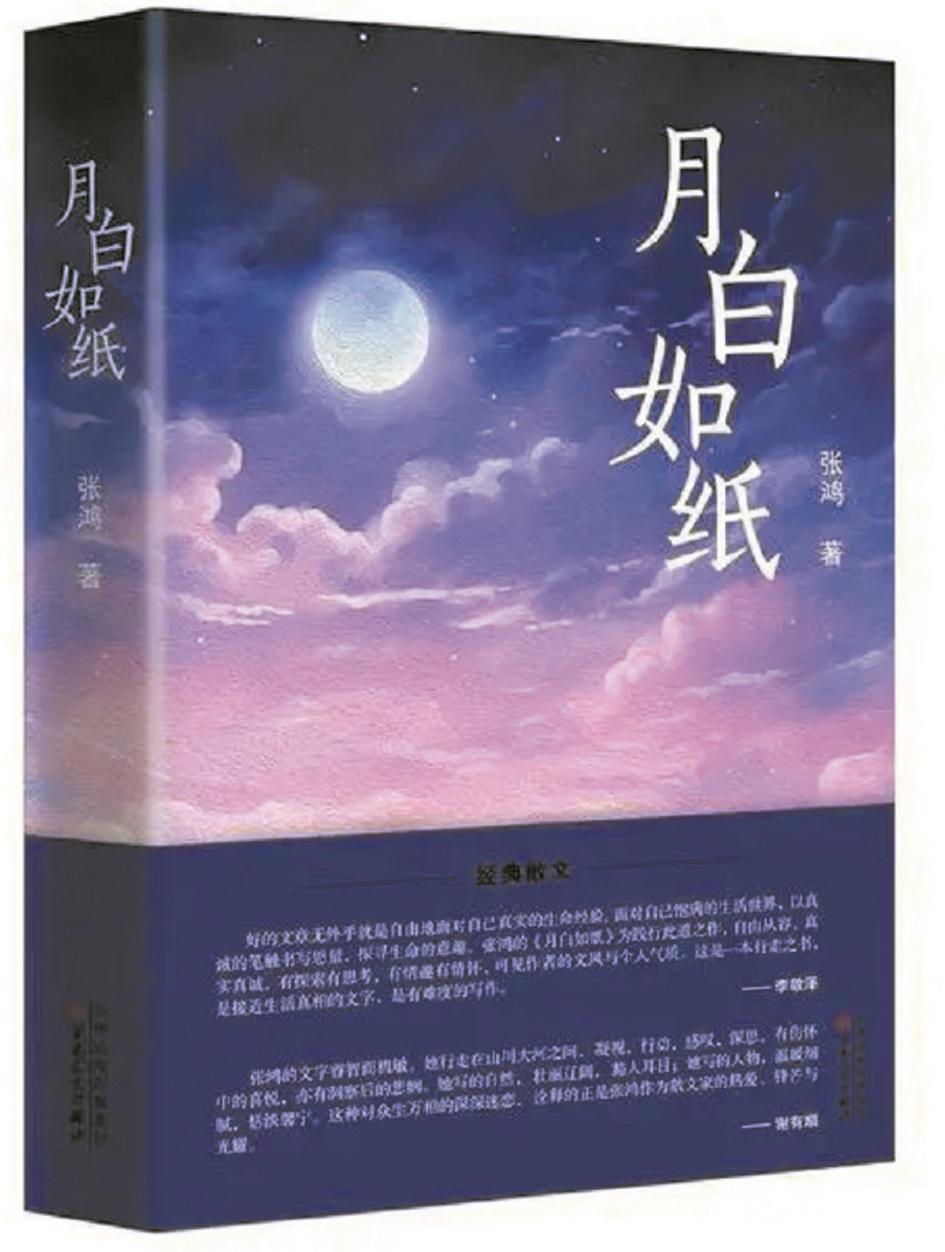河南 □楚些
对于散文来说,精神个体性在白话散文史上可谓常言常新,精神个体性的呈现大致有两种向度,一种来自自我独特的成长经验,另一种则来自个体与群体间咬合过程中得到的镜像,通过镜像的确立和反观,精神个体性得以丰富,得以拥有弹性的区间。《月白如纸》中精神个体性的呈现大体上来自后者,即通过读取他者获得内心情感的摇动和精神世界的静观。
这种对他者的读取,使得这部散文集中的诸多篇章在类型上可归入人物散文的范畴。源于新世纪以来叙事的转向,人物散文趋于丰盛,并寄生于乡土散文、亲情散文、历史散文等不同的题材和体式之中。其基本面貌有二,人物成为叙事单元或者叙事主体,无论是作为单元还是主体,在具体的作品中往往承担两种功能,一种是社会学性质的,表达作家的现实关怀和反思力度;另一种则是私人性的,呈现作家的情感寄予和镜像反省的内容。《月白如纸》中,张鸿笔下的人物群像以陌生人为主,他们在远方,在异地,因为“我”的出行而偶然交集。这种偶然性的交集,类似于高更笔下的瞥见——仅此一瞥,便可激起灵魂深渊的记忆!《山高谁为峰》中有对作家同行的素描,重点勾勒的则是帕里边防派出所干警的群像。这群老练持重的年轻人中,有心怀成为儿童作家梦想的龙熙,在高原极地不忘阅读与写作。有女警官王艺儒和她养的一只叫可可的小狗,荒寒之地,军装之下,仍然有一颗跳动的热爱生活的赤子之心,而小狗可可咬鸡的行为则让人又爱又恨。动物的天性和人伦法则起了冲突,恰构成戍边生活的插曲。总之,在这群承担特殊任务的边地干警身上,他们既有着养鸡种菜、养狗狗及拍摄微电影的日常,也有着数日蹲伏于边境线上,忍受酷寒、孤独、黑夜的吞没而不发一声的敬业。他们的人生片段所卷起的边角,构成了生命存在厚重而多元的画卷。《新疆老张》一篇中的老张,是一位转业军人,专跑新藏线,熟悉路况也熟悉人情和地方风情。在话痨和油滑的表象之下,实则隐藏着对女性的尊重和细致体贴,更不一般的是,在康西瓦这一海拔近5000米的达板处,他抛下众人,带着香烛、白酒、香烟进入落寞的烈士陵园,在战友的墓前坐下,清理墓碑,奉上祭品,嘴里念念有词。在这样的言语细节里,最真实的老张突然面目清晰起来。《高佬》中的高佬来自湖南,是作家所在小区的废品回收者,日常虽喜欢小酌,但在交往细节中,古道热肠以及心思细腻之处尽显。像高佬这样的人,是每个人都会遇见的他者,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,“孤岛”得以紧紧相连并息息相关。
张鸿有从军经历,其笔下除了战友的素描之外,与陌生人的交往过程中,对于曾经的军人身份拥有特殊的敏感性,彼此之间也很容易产生心灵的同频,像北疆的艾斯肯老人,还有西南边陲小城里的公交车司机,皆成为其人生读取的重要内容。
《月白如纸》有两位人物为存在可能性的疆域提供了更加宽阔的向度。第一位是寓居于敬老院已届耄耋之年的蓝阿姨,她在儿女关系上的豁达,她与来访儿童间的嬉戏和契约订立,还有其散文《夏夜》中的野性和烂漫,很容易让人想到人性的完整性这一词语,以及这一词语引发的张力。另外一个则是《奔子栏此里卓玛》中的卓玛,一位被当地人称之为“疯子”的女性,她可以放下婚姻,随性离开拉萨,在茶马古道曾经的重要渡口,甫一见面,不由分说地拉着“我”野游。她的自由不羁,如梅里雪山的雪崩。只有卓尔不群的边地思维和文化系统,方能够结出如此透彻的边地之花。她的人生,不由得让人叹为观止。
我们习惯了慈爱的日常,而文学所供给的会有B面,很大可能是出格的景致,而正是因为出格,方会让人们停下来,进入沉思之境。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