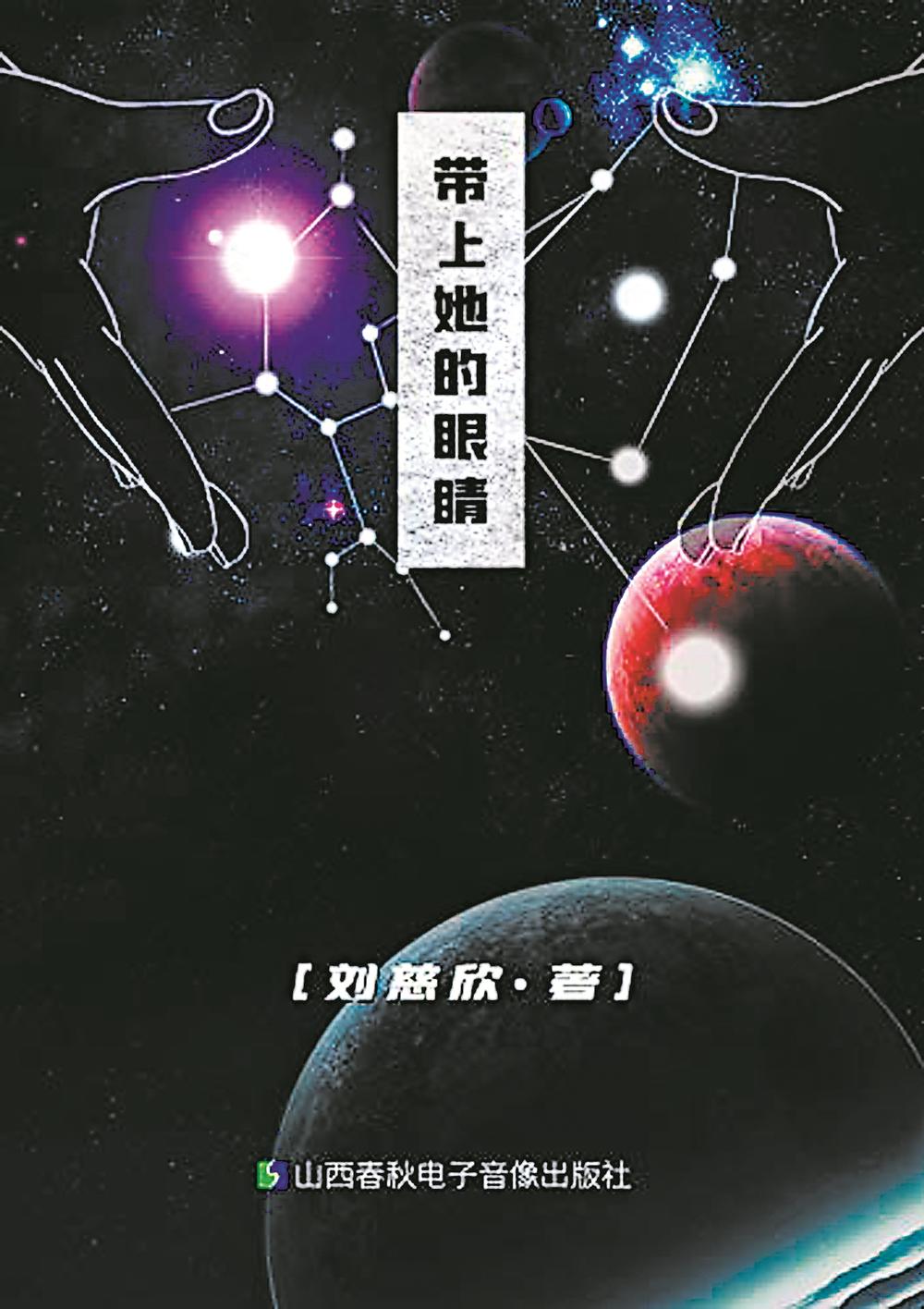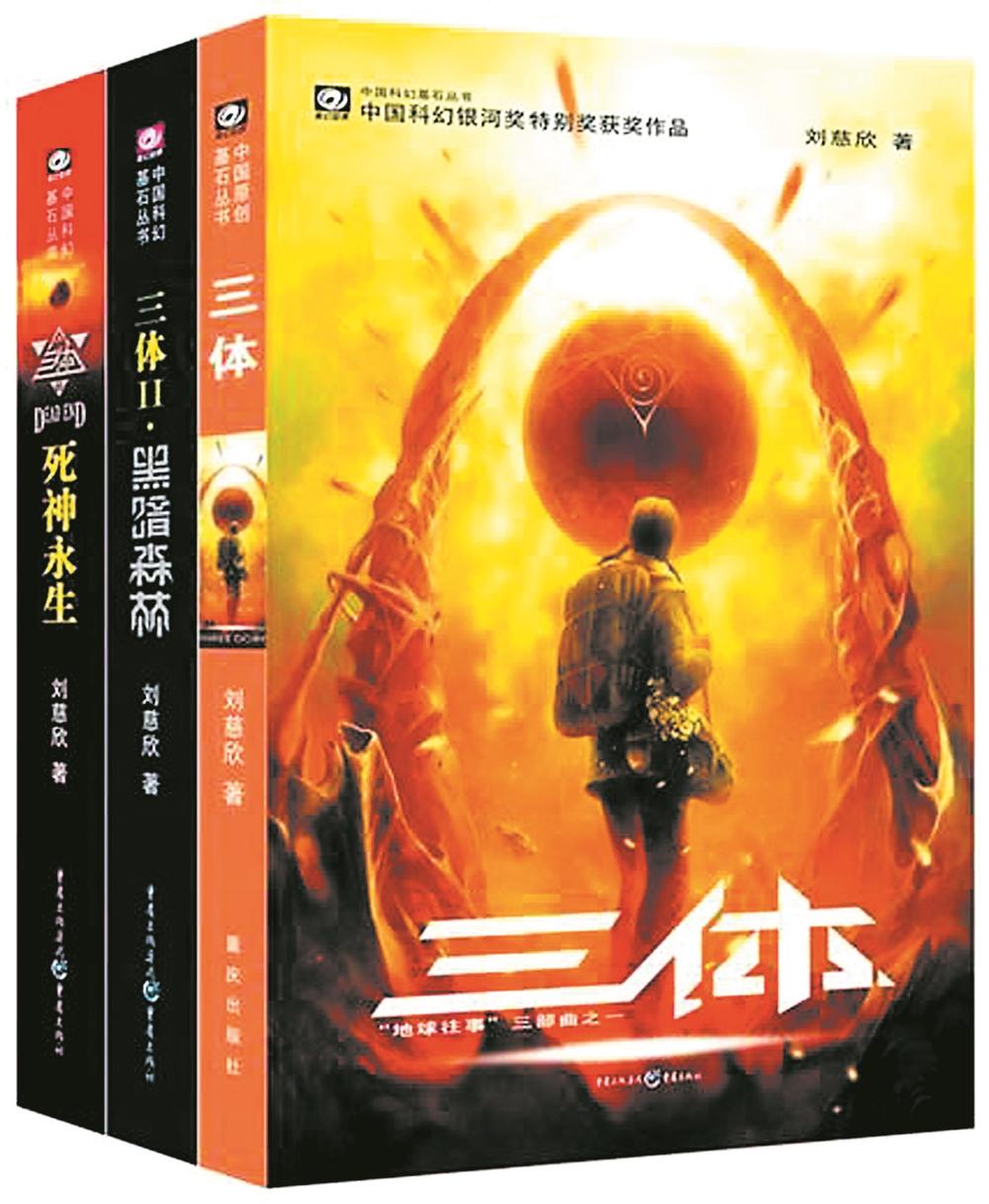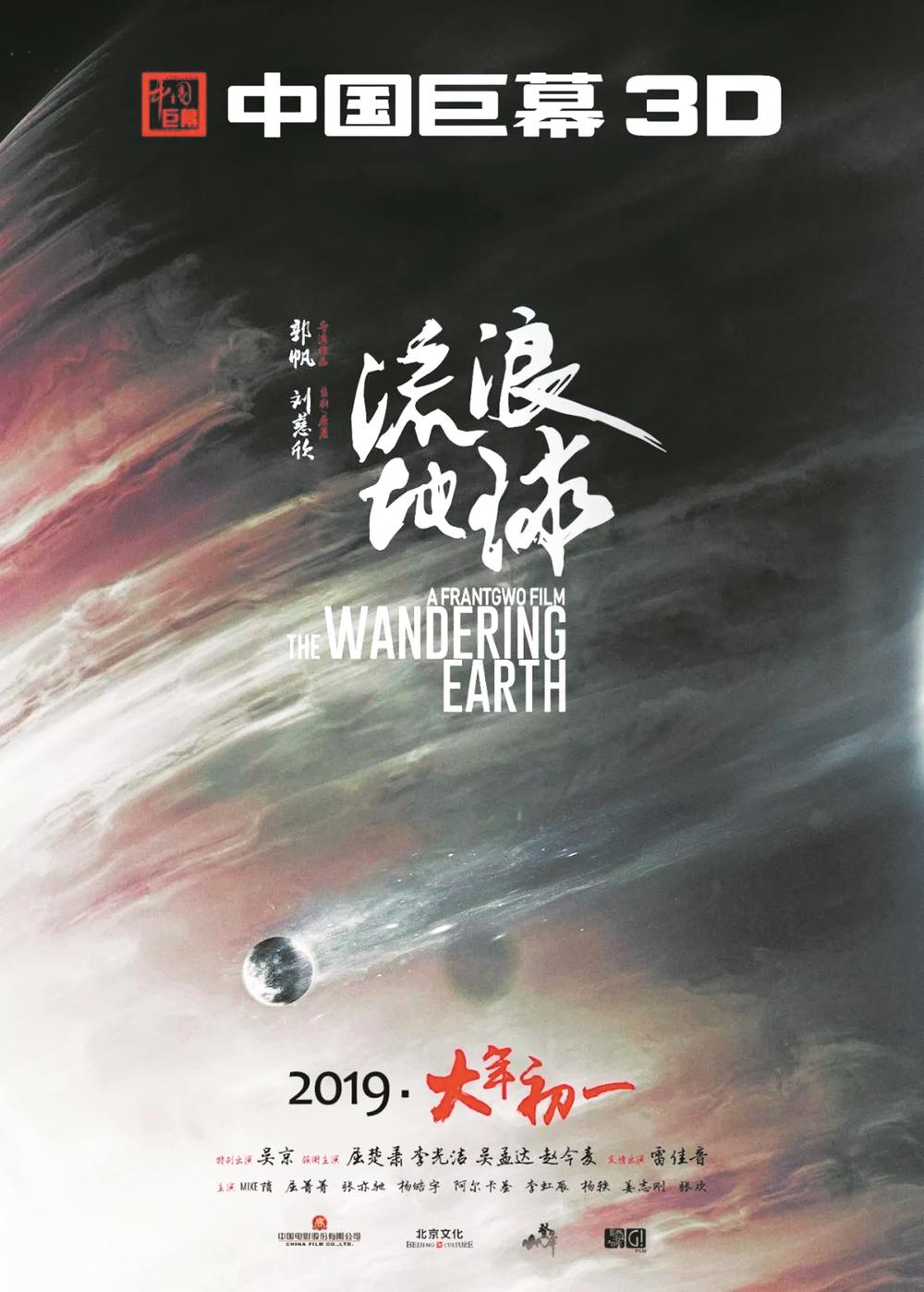刘慈欣,山西阳泉人,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之一,代表作《三体》三部曲、《流浪地球》等,其中《三体》在2015年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,为亚洲人首次获奖。《三体》被公认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,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。2019年刘慈欣作品改编的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和《疯狂的外星人》进入当年内地电影票房前十名,其中《流浪地球》以46亿元成为票房亚军。
不走文学化的道路
1999年,我在青城山(参加第一次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笔会)。当时阿来请了《小说选刊》主编冯敏来给我们讲什么是文学,意思是说,我们这些写科幻的(在)文学上不行,给我们普及一下。
当时我发表了两篇小说,《鲸歌》和《微观尽头》。那会儿同时投稿五六篇,能发表就很不错了。之前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东西,也和《科幻世界》没有联系。另外几篇是《带上她的眼睛》《地火》《流浪地球》《西洋》,还有一篇没发表过的战争题材科幻小说。比较保守,选的是两篇最短的,连《流浪地球》都没发,后来是2000年《流浪地球》才发表……
当时国内科幻不像现在,有这么多的发表渠道,也就是《科幻世界》和山西《科幻大王》两家,大部分作者都在《科幻世界》发表小说。每年发表的空间就那么点儿,能发表就很不错了。(《带上她的眼睛》获1999年中国科幻银河奖),肯定是一个鼓励。
(2000年左右正好是中国科幻的一个“井喷期”,很多优秀作家集中登场亮相,比如赵海虹、柳文扬以及周宇坤等,而且发的都是重量级作品甚至代表作,这些人现在都是成名作家。那时获银河奖非常不容易。)
其实在那之前我也在创作,但作品没给任何人看过,不管是科幻读者还是身边的人。所以我也没有发表的把握,自己感觉那五六篇稿子和当时流行的科幻小说差别挺大,也没把握能获得他人的认可。(《科幻世界》)编辑给我打了电话,说你那些小说都很不错。我才知道这种写作风格还是可以的,并不完全另类。那是我第一次和科幻界的人联系。当然很高兴,但也没觉得太怎么样。坦率说,当时写科幻小说是一个很业余的爱好,并没有把它当事业去做。那会儿工作也很忙,真正能顾得上写科幻的时间不是太多。
我买过很多期《科幻世界》来看,看了后觉得我这种写法肯定不行,就模仿《科幻世界》当时流行的风格去写,像《鲸歌》就是很典型的《科幻世界》风格。后来发现不需要那样,《科幻世界》之所以是那种风格,是因为没有像我这种风格的作者投稿,投稿的话他们也会发的。
(《科幻世界》当时的风格是)故事性强,但世界架构不大,没有很大、很终极的世界观,并不很强调文学性,故事清新流畅、适合年轻读者,故事里面文学性、人性的东西不能和科幻很好融合,比如,爱情就是爱情,科幻就是科幻,两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关系。可能也是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吧。
(从青城山)回去后,我仔细想了想,发现了一个人们忽略了的事实。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,列出了100部最顶尖的文学名著,角度很有意思,不是从文学本身去评价,而是去调查文学名著在当初市场上的销量,调查结果令人震惊:100部文学名著中,95部都是畅销书,像《尤利西斯》那样卖出200本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少之又少。
那会儿我就坚定了信念,不走文学化的道路,必须面向大众、面向读者。我觉得这个创作方向是没有错的。
获得银河奖后我又发表了《流浪地球》和《地火》,然后就是阿来约的专辑《朝闻道》《梦之海》《中国太阳》三个短篇,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,这要放到现在是不可能的。当时有大量的创意挤在那儿,要表现出来,写得十分快。现在读者都成熟了,见的东西多了,但那会儿大家都没见过这样的硬科幻创意,所以拿出来效果都很好。
写作是一种消耗
(有意识地自主写作)我比较早,高中的时候就写过科幻。我一直有个遗憾,不管是我也好,还是整个科幻(界)也好,我觉得错过了什么东西。我现在最后悔(觉得)做错的一件事,就是一个文学界前辈跟我讲的:“你认为写作是一种积累?错了,写作是一种消耗,耗着耗着就没了。”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了他这句话。要注意,不要都耗完了,廉价地耗完了。
写那么多的短篇干什么?我在《科幻世界》杂志发表的三十多篇中短篇小说,几乎都是长篇的题材。我一直在想,如果那些小说全以长篇形式发表的话,现在是什么样子?哪怕只有一半写成长篇,现在是个什么局面?但没办法假设。
我一度想过,不要写了,等有了发表长篇的渠道再写。挥霍题材,这样下去很快就完了,耗完了就没有激情了。读者没了激情,作者也没了激情。科幻就(是)这么个东西,创意很重要。哪怕把当时那些创意留下一部分也行。
文学就是一种消耗,积累不下什么东西,你有多少积累就写多少东西,还指望能越写越多?当时我还不相信他的话,觉得我的创意无穷无尽。哪有那回事?
《三体》原是另一个故事
2005年左右,我写完《球状闪电》后就开始想写《三体》。当时写这本书,并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大的影响,不管是我,还是《科幻世界》,都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长篇小说来对待,没想到在其中投入那么大的力量。第一稿写得比较随意,想快点写出来就算了,后来做了很多的修改。
《三体》最初的驱动力是两部作品。一部是小松左京的《日本沉没》,这个作品很震撼,也很适合中国读者的欣赏取向。我想写一部中国版的《日本沉没》,但我们没有日本那种岛国的忧患意识。我甚至想写陆地被地质活动分割成一个个的岛屿,后来发现也不好弄。
另一部作品,是吴岩跟我说,他想写一个“中国轨道”,大概讲20世纪60年代发射航天员上太空的故事。这让我也想写一个相同背景的科幻小说。
我做了大量调查,调查相关历史、看过很多档案,还去当年的那些地方看过。但后来和一些“80后”读者交流,发现他们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,我就把那个想法放弃了。我们的科幻是给这一批读者看的,又不是用来怀旧的。我想那么写,很大程度是一种怀旧心理在作祟。最后我就放弃了那个想法。
(那个)一直打算写的版本,想得很成熟了,最后决定不写了,所以现在这个《三体》版本,其实构思很快,也很匆忙。当时本来想,写完第一部就算了。第一部的结尾都想好了,就是模仿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,一个老师给学生讲最后一课,外星人要来了,你看看人类5000年都干了啥?时间都耽误了,明明能够把精力放到技术突破上,结果在太空中毫无进展,最后一直等到现在,什么办法都没有。后来觉得还有好多能写的,才有了第二部、第三部。
我不想把一本书写得那么长。说实话,像《冰与火之歌》《哈利·波特》这样的作品,除了热衷的粉丝外,让一般的读者从头看到尾,也不是太容易。《三体Ⅲ》字数太多了,已经够长了,越长越难让人看完。三本已经够长了,比较理想的长篇就是一本,或者上下册都可以。
总的来说,我感觉,创作首先得有一个平常的心态。好的作品它要出来,它的命运在那儿,自然会出来。不是说,我想把它琢磨成多好的东西,出来就是多好的东西。有些是很不经意间就成了很好的东西,反而是郑重其事地想写一个多好的,最后不尽如人意。
文学不是有志者事竟成
(《三体》获得雨果奖之后)绝对没想到它会在那么多国家受欢迎。当时《三体》英文版签约的时候,在北京还举行了一个仪式。我心里没把那个当回事儿,心想,这东西有什么前途啊?当然出个英文版也不错,至少让美国知道中国还有科幻。那个仪式挺隆重的,大家都郑重其事,就我觉得这东西(虽然)也不错,但真没有太把它当回事,确实没想到后面会有那么大的影响。
现在看来,我当时的想法特别可笑——我自己的书我都不在乎,你们费这么大的劲儿干吗?《三体》的幸运不可思议,甚至得了雨果奖,简直有如神助一样!怎么排在第六名的,正好有个人就放弃了?这在雨果奖历史上都极为少见。
所以我跟很多年轻作者说,在文学创作上要成功,肯定有你自己努力的原因、有你的才华和作品的原因,但还有一个很重要,那就是机遇。机遇和前面那些东西不一样,它不是由你自己来把握的。你觉得你写得很好,付出了巨大努力,但你的作品不被承认,有两种可能:一种可能是你高看了自己;一种可能是你确实写得很好,但错不在你。这个机遇不是你能把握的。在文学上,不是有志者事竟成,没有机遇不行。没有各个环节的人去做共同的努力,根本就不行。
所以我一直说,文学并不是一个行业,不像医生、教师、工程师,这些行业你只要努力,可能取得成功的程度不同,总归会有一定成就,但文学确实不是那样。除自己之外,别人的努力,还有大时代的环境,都是十分重要的。最后就是运气十分重要,得雨果奖那就是运气,真的这不是我谦虚。
在芬兰的科幻大会上,刘宇昆(注:科幻作家,《三体》英文译者)把弃权的那个人介绍给了我。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人对你影响特别重大,这个人对我影响就特别重大。不过我没法对他说什么,他弃权也不是为了我,我也没什么可以感谢人家的。面对着对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人,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好在这时候过来一个航天员,就是在空间站上宣布我获奖的那个,这才缓解了尴尬。
机遇和实力不是x加y的关系,而是x乘y的关系,一个为0就全为0。我跟《流浪地球》的剧组说过,他们也承认,这个电影很幸运。
(摘编自《中国科幻口述史》,杨枫编著,有删节。括号内文字为编者补充)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